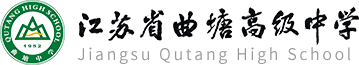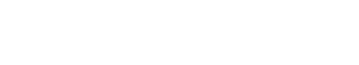网上校史馆
情系母校
首届校友陈寅生的回忆录
田野的花儿
陈寅生
1952年夏天我从曹庄小学毕业和蒋中元大哥的小妹蒋静兰一起考进了海安县第二初级中学——曲塘中学的前身。
1950年夏天,我在曹庄小学读了一年四年级后顺利地拿到了初小毕业证书——那时社会上还有“百字先生”,识100个字就能做先生,初小毕业,已经是很有文化的了。那毕业证书是县人民政府发的,上面盖着四角方方的“海安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中间是毛主席的戴着八角帽的画像,十分庄重。细细想来,初小四年我只上了不足一年半,曹庄小学1年,培德小学不足一学期。另外上了一个月的私塾和一个月左右的识字班。这一直让我引以为荣,并潜滋暗长着骄傲自满情绪。
那时高小毕业已经算是文化人了。山东有位女生叫徐建春,高小毕业后回乡劳动,中央就号召全国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向她学习。
1952年海安县只有3所初中:第一初级中学(即迮庄中学),第二初级中学和民办性质的紫石中学。各个学校单独招生,有先有后,一个学生可以赶考好多次,我考第二初中时,也是十几个考生中才录取一个。我年纪小,个子小,胆子小,不知事。我是大姐梅生驮在肩送我去赶考的。那时考取了初中,比现在考取大学还光荣神圣。那年我们村里只有我一人考取了初中。
第二初中最初办在王家楼一户地主的庄园里。这是一所两进带东西厢房的建筑群,30多间青砖青瓦的古旧平房里,住了100多名学生,分为甲乙两个班,我在乙班,蒋静兰在甲班。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我最小,12岁,大的20多岁,据说有的人已经结了婚。
整个校园像个“曰”字,东厢是厨房及工友宿舍,西厢是男生宿舍,后排是两个教室,中间是教师办公室、教师宿舍以及女生宿舍。前面是院墙。宿舍里没有叠床,老师和学生都是木板搁铺,高低宽狭不一。宿舍里没有太多的规章制度,女生也可以进男生宿舍。那时我常常尿床,尿了床之后又不好意思晒被子,比我大5岁的蒋静兰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男生宿舍来拉开我的被子看一看,如果被子尿湿了,她立即拉出去晒,有时还把我的脏衣服收去洗。蒋静兰十八岁了,我们宿舍里也有十八九岁的男生,大家都规规矩矩的,从没有什么越轨行为。那时没有《你漂亮我潇洒》和《真的好想你》之类的歌曲,大家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的心纯洁得像一碧如洗的蓝天。
那时还没有实行“统购统销”,不少人家都是推着独轮小车装着大米来抵算伙食费或别的什么费用。学生8人一桌,中午一桌一盆青菜,一周一次大荤——青菜上加一大铜勺红烧肉。我年纪小,吃得少,每逢大荤,总有大同学生夹两块瘦肉给我,然后再夹两筷子青菜,我泡点汤,三扒两咽就吃好了。他们吃菜,也总是礼让或各守本分。饭,随便盛,尽吃。
当天的作业当天都能完成,晚上也就两堂自习课。傍晚,有较长的活动时间,不少人到东边操场上打篮球。到南边胡集区公所里打乒乓球,或者在教室画画练唱歌。我是常常在教室抄简谱,练唱歌。生活丰富多彩,愉快充实。
1952年秋天,政府拨款在曲塘北面的“小圩子”里砌新校舍。老师们常常十分兴奋地描绘新校舍砌得如何好,窗子是怎样的大,墙壁是怎样的白,台阶是怎样的高。建筑工人辛苦了,于是大家自动捐款,派代表去曲塘慰问建筑工人。
曲塘的新校舍砌好后,1953年秋季开学时,我们便搬迁到曲塘去了,并增添了西场等地的两个初中补习班。校名也改为“曲塘初级中学”。从此,王家楼那青砖瓦房就“凤去台空”了。
现在想来,建国之初,我们这批农村青少年中学生多么淳朴啊!不矫揉造作,不虚张声势,不声嘶力竭,像田野的花儿,自然流露着芬芳,沁人心脾。
2003年春天写于海安
我热爱我的祖国
我热爱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的安危、祖国的兴衰、祖国的荣辱都牵动着我的心,牵动着我大脑里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我为她警觉,为他兴奋,为他欢笑或流泪。
屈原沉江汨罗,苏武牧羊北海,岳飞精忠报国,这一个个感人的爱国故事昭示着我们民族步履的蹒跚和祖国历史的沧桑,在我刚刚知事的时候,就随着长辈和在外读书的哥哥姐姐们的讲述而植入我幼小的心灵,让我感动,让我激奋,让我久久回味。
后来,读小学了,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歌声,悲壮哀怨,如泣如诉,浸入我的心田;岳飞“怒发冲冠”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如鼓如雷,震撼着我的心房。我一人独自轻唱微吟时,这歌声好似精灵,融进我的血液,在我周身流淌,涌动。
读高小时,袁汉才老师慢言慢语而又略带几分义愤讲述的关于“红头阿山”(从前上海人对流亡在上海的印度人的称呼)当亡国奴的故事,让我想起幼年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时全家人坐船躲到草荒田里的可怖情景。从那里起我渐渐懂得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初中里,我有幸成为升旗手。当刚刚升起的太阳给大地镀上一层金辉时,当金辉下的全校师生整整齐齐地列队在操场上时,当操场上空响起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时,我随着这激奋人心的旋律拉升着五星红旗,我感受到身后一片目光都在向国旗行注目礼,我感受到祖国是神圣的。天长日久,神圣的祖国在我心中有了具体形象——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当张积慧在朝鲜战场上击落一架又一架美国飞机时,当陈镜开打破轻量级世界举重纪录升起五星红旗时,当周总理登上万隆会议讲坛发表演说时,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年轻的共和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在曲塘这偏僻小镇的校园里,不时涌动着同学们不无自豪的议论和欢呼。在《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歌声中,我们的眼前逐渐显现出一条需要我们去参与开拓的金光大道,于是大家都发奋地努力着。
我读初二时,曲塘中学已经有了图书室,学生可以借阅图书,于是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我,不少课余时间都花在看书上。我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看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背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整理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的记录,这些诗文报告感染着我,在我少年的心中产生过许多次要为祖国横枪跃马、驰骋疆场的幻想和冲动。但幻想最终未能变成现实,冲动最后还是平伏下来。我只有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将自己的所有的零花钱都捐了出去,以表达我这个贫穷学子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从此之后,爱国之情,报国之心,便在我心中立定根基,不可动摇。当祖国蒸蒸日上时,我为她欢呼,为她歌唱;当阴霾满天时,我为她悲伤,但不丢失希望——因为祖国还在。祖国总是给我以生活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历史的传承,是生活的感化。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政治课上那冗长而枯燥的说教;大会上那激昂而空洞的报告,都被时间的流,滤去了,只有生活中的感受才铸就了我这颗爱国之心。因此,我以为:教育应该生活化,生活应该教育化,这对于思想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少年儿童来说尤为重要。
2005年1月18-19日写于银杏院
各具特色的老师
1953年初秋,我们在曲塘中学读初二时,学校里有20多位老师,这些老师各具特色。
那时我个子小,从初二到初三,总是坐在第一排。上几何课时,我的几何课本常常被一只沾满粉笔灰的大手夺去——那是我们的几何老师王君律先生要用几何书了。他第一次夺书,我有点吃惊,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王君律先生,紫红色的脸上有些皱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有点怕人,他经常穿一身蓝得有点发红的半旧衣服,那衣服上总是沾满粉笔灰,尤其是冬天穿的那件旧棉大衣,污垢和灰尘足以将一大盆清水洗稠。他上课常常不带书,上课钟一响,前门卷进一股风,那是王君律先生抓着大三角板冲进教室了;教室里响起洪钟般的声音,唾沫星子在我头顶上飞舞,那是王君律先生在讲课。他讲课时,眼睛总是望着天花板,需要作图时,他才转过身去。倘使急需擦黑板,他便竖起右边棉大衣的袖子,由里而外边走边擦,边擦边讲。“什么叫射线呢?”他边讲边在黑板上点一点,然后边画边走,边走边说:“从任意一点向一个方向上无限延长,无限延长,无限延长……”他人已经走到教室门外去了,粉笔线也画出了黑板,画在墙上,他仍然在说:“无限延长,无限延长……”然后回到教室里说:“这样的线,就是射线。”王君律先生上课就是这样的洒脱而生动,所以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
徐石清先生教我们的代数,50多岁,秃顶,尖下巴,一脸的大黑麻子里嵌着一双亮亮的小眼睛,说话尖而响,有人说他很凶,其实他做事非常严谨。他上课时黑板总擦得干干净净,算式总写得整整齐齐,推导一步接着一步,步骤十分严密。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极严,“等于”必须用三角板画平画齐,演算步骤有一步错了,总必须订正。代数有甲乙两本练习册,每天轮流着交,这样,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他也有充裕的时间批改。我经常看到他,除了上课,总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备课。
黄留章先生是黄桥人,脸色黄黄的,说话温柔,有点娘娘腔。初二时教我们的物理,初三时教我们的化学,写字时多用彩色粉笔,故意写得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那时我觉得很有趣。更有趣的是他上课时做的理化实验。有一次,他拿出两个带手把的半球形的铁东西,将它们合成一个铁球,然后将里面的空气抽掉,叫两个力气最大的男同学上前去拉,那两个同学怎么拉也拉不开,我们十分惊奇。这时,他说:“这个铁球,叫马德堡半球,是做大气压强的试验用的,16匹马也拉不开”,大家听得非常专注。黄留章先生总是将理化知识的传授贯穿在实验之中,讲得生动而风趣,让我们乐于学习,易于理解。
我们的历史、地理、植物学、动物学等课,都是年轻老师教的,这些老师生气勃勃,讲课时充满热情。
王君律先生的洒脱,徐石清先生的严谨,黄留章先生的风趣,年轻老师们的热情,把我们带进了知识的海洋。那时没有太多的作业,当天的任务都能在不太紧张的气氛中完成,我们有时间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时间读课外书籍,有时间琢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一天,我在心算两位数乘以两位数时,突然发现一条规律:只要十位数相同,个位数相加等于10就有一个简便的算法:例如33×37,可以变为30×40+3×7=1221;再例如:45×45,可以变为40×50+5×5=2025。当时我一阵惊喜,但也没有张扬,因为这样的小发现不止一两次。
现在想来,那时没有使学生陷入被动的应试教育,因而智力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学习史地和生物,还让我逐步摆脱了愚昧和迷信。小时候巫婆给我治过病,又听过许多鬼怪的故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怕鬼,刚上初二时,晚上我一个人不敢去上厕所。学习了这些科学知识后,逐渐相信世界上没有鬼,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逐渐植入我的大脑。
我们的校长叫肖葆初,40多岁,左眼瞎了,右眼视力也不好,看书时,总是用右手拿着,放在靠右眼很近的地方。他不苟言笑,也不威严,给人清冷的感觉。他曾经给我们上过课。他说:他结婚没几天,就离家参加革命去了,年轻时由于看书太多,眼睛疲劳,经常用不卫生的东西揉眼睛,眼睛就不行了。他关照我们要保护眼睛,话语中流露出慈祥和关爱。有一次,我带来缴伙食费的两块钱少掉了,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找我谈话,了解情况,我只是哭,他像慈父似的轻言慢语地安慰我,为我擦眼泪,帮我到宿舍里仔仔细细地寻找,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在他彻底了解了我家经济的窘迫情况后,他为我缴了那个月的伙食费,并将我的人民助学金提高到每月3.2元。那时伙食费每月大约是五六元吧!他对我说:“这人民助学金是祖国、人民用来救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习的,你拿了这么多助学金,要好好学习。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就要到来,需要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学习好了,将来就有本领报效祖国!”我知道肖校长是老革命,是共产党员。肖校长的关心让我感受到祖国和人民的暖温,感受到共产党的温暖。
幸福的歌声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我依稀记得,三四岁时,只要在外读书的堂姐姐们脆声细气地唱起甜美的歌曲,我便跟着学唱起来,于是姐姐们便围拢来逗我,教我唱歌;后来上小学和初中了,校园里飘出的歌声总让我感到温馨而甜美。我以为校园里不能没有歌声。没有从学生口里心里流淌出甜美歌声的校园是压抑的,沉重的,可悲的。
歌声是情绪的渲泄,是情感的交流,是生活的需要。它无影无形,却有色有味,入耳牵心,移情动性,给你留下永久的情绪化的形象记忆。许多年过去了,只要你听到曾经感动过你的那首歌,当年的人物和事件,当年的场景和氛围,当年的情绪和感受,就会涌入你的心头,于是我想起在曲塘中学读书时那幸福的歌声来了。
那是1953年初秋,我们搬进了刚刚建成的新校区,那围着竹篱笆的宽广的大操场,那墙壁雪白窗户明亮的新教室,那地面平滑叠床整齐的新宿舍,那有序有味而不太紧张的课堂学习,那多彩多姿丰富有趣的课外活动,那琴声中的早操,歌声里的中餐,总让我们这些从农村茅草屋里走出来的贫穷青少年感到无限的幸福,于是那幸福的歌儿便自然地从我们嘴里心里流淌出来——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毛主席啊共产党,
哺育我们成长……
我们歌唱幸福礼赞祖国,礼赞伟大的领袖和共产党。这是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的心声,不矫情,不造作,顺理成章,自自然然。
那时每逢集会,正式开会之前总要拉歌、唱歌。这个班拉那个班唱,那个班拉这个班唱,每班都有一个拉拉队长,这个班的一首歌刚唱完,另一个班的拉拉队长便站起来高声叫道:“唱得好不好呀?”他班上的学生会齐声叫道:“好!”“要不要再来一首?”“要!”“一二三!”“快快快!”“一二三!”“快快快!”于是歌声又起。就这样,一波连着一波,高潮接着高潮,笑语洒落一地,歌声飞上云天,宣泄着年轻人的欢乐、幸福和自豪。
这样的拉歌,有拉集体唱的,也有拉个人唱的;有拉学生唱的,也有拉老师唱的。拉老师唱也是“一二三!”“快快快!”如果老师迟疑不唱,拉拉队长还会拖长腔调来一声“咦—”全体同学紧接来一句话:“他又不唱的?”“一二三!”“快快快!”于是教师清一清喉咙便唱起来了。无需开导,无需说教,师生的感情自然平等地融会到一起了。
我最不会忘记的是蔡志中老师唱的那首四川山歌《太阳出来暖洋洋》。
那浑厚的男中音如古刹的钟声在山间回荡,又似大海的惊涛拍打着礁石,那么有力度,那么有气势。若干年后,我听著名歌唱家温可贞在南通文化宫三厅演唱时,大脑里立即显现出蔡志中老师唱歌的情景,我觉得蔡老师可以与这位歌唱家一比高下。
蔡志中先生是体育老师,弹得一手好琴。学校里没有广播体操唱片,我们每天做早操,总是一个老师喊口令,蔡老师用风琴弹广播操的乐曲,风琴旁边放着一台麦克风,口令和琴声配合得十分和谐,我们便在这和谐的韵律中享受着健身的乐趣。
活动课是绝对没有老师把我们关在教室里上课或考试的。球类、田径、歌咏、舞蹈……学校里把每个班的课外活动都安排得那么井然有序。每到活动课,校园里便成了欢乐的海洋。操场上,打篮球的,踢足球的,跳高的,跳远的,荡秋千的,越跳箱的,龙腾虎跃,热气腾腾;教室里,练习大合唱的,小组唱的,独唱的,歌声飞扬,热情洋溢;教室前的天井里,围成一圈跳铃鼓舞或邀请舞的,舞步杂乱,笑语喧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我们活泼健康,热情开朗。
那时我们有一位全县最好的音乐老师,叫王子平,是刚刚大学毕业的。那时一个音乐系毕业的大学生可了不起,听说她到海安时,是县委宣传部长去汽车站迎接她并为她扛行李的。她小巧美丽,歌喉甜润,甜润得说话也像唱歌一样好听。同学们都盼望她上音乐课,每当风琴抬进教室时,同学们便是一阵雀跃。
她教我们唱一首新歌之前,总先唱一遍给我们听听:
在卡吉德洛古老森林,
有一股清水泉,
又明澄,又清洁,
又凉快,又甘美,
好一股清水泉。
那甜美的歌声犹如一股甜美的泉水缓缓流入我们心田,让你凉快、舒服,神清气爽。
“同学们,这是一首波兰民歌,轻快甜美,好好学吧,散步时唱唱,挺好的!”她那如唱歌似的话音一落,我们便随着她的琴声认真学唱起来。
王子平老师还给我们系统讲授乐理知识,指导我们练习“视唱”。那时,没有音乐教材,每次上课她都发油印的音乐讲义,那讲义上的字比王老师写的字好,听大同学说,有好几个年轻的男老师都抢着为她刻写讲义呢!
自从蔡志中老师和王子平老师来了之后,不仅活动课里有了歌咏和舞蹈,连吃饭时也听到甜美的歌声了。学校在前排教室中间的过道里安装了一台麦克风,每逢我们坐在教室里吃中饭时,麦克风前便有人唱起歌来,那些人大多是各班的优秀歌手,也有老师。那甜美的歌声将我们普通的中餐变成了天上的盛宴。我们因幸福而歌唱,因歌唱而幸福。我曾经绘声绘色地向妈妈介绍过边吃饭边听大喇叭里飞出歌声的情景,我喜滋滋地说:“妈妈,我们已经过上社会主义好日子了!”母亲笑了。
我原先懂点简谱知识,王子平老师教了我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按简谱唱一般歌曲了。我喜欢唱抒情歌曲,尤其喜欢唱缠绵哀怨的陕北民歌《兰花花》,也喜欢唱深情悲伤的《牧羊姑娘》,我觉得那旋律、那情调特别合我的口胃,现在想来,也许由于我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的缘故,这样的歌曲渲泄着我郁结在心中的悲苦吧!但我独自轻唱的时候,我只为歌曲中的两位姑娘的不幸遭遇悲伤,我自己倒感到歌唱的愉悦,那种愉悦来自自由自在的抒发、挥洒和张扬,因此也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独自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常常唱起那首波兰民歌——
在卡吉德洛古老森林,
有一股清水泉……
于是,一股明澄、清洁、凉快、甘美的泉水便流入我的心田。
因为生活中有了歌,世界才有了更多和谐的声音,更多美丽的色彩,更多美好的形象,也才有了更多灵性的发掘和探求。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独自一人散步时,还常常轻声唱起王子平老师教的那首古老的波兰民歌,唱起在曲塘中学学会的那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歌曲,于是当年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便呈现在眼前,于是感受到少年时唱歌的那种幸福。
2005年1月21-22日写于银杏院
远去了的学友
我于1955年7月初中毕业于曲塘中学。50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年的不少同学已经从记忆中淡去,但是,蒋静兰、陆兆荣、蒋琪等同学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蒋静兰是我小学里的同学,比我大5岁,我们在王家楼读初一时,她一直像姐姐似的照顾着我。那时我常常尿床,不好意思将被子捧出去晒,她虽然与我不同班,却常常到我的宿舍里查看我的被子,常常把我的被子捧出去晒,从来没有责怪过我。
后来上初二了,到了曲塘,男生女生都多了,男生宿舍在西边一长排,女生宿舍在东边一长排,中间隔着一堵墙,她就很少到我宿舍里来了,我也极少尿床。但她还常常关心地问问我生活上的情况。
曲塘到我们家40里,都是田间小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那时我回家都是和蒋静兰一起跑。
寄宿生回家的星期六下午,学校是不上课的。吃过中饭,我背着大姐缝制的灰布书包,里面装着脏衣服和几本要看的书,早早地守候在通向校门的大路边。不一会,蒋静兰背着花格子书包一摇一摇地走来了——她矮、胖、平足底,走起路来留给我的印象总是摇呀摇的。
“走啊?”我问她。
“你东西都收好了?”她问我。
因为我曾经丢失过两块钱,很伤心的。每次回家前,她总关心地问我放在学校的书籍及衣服等东西有没有收拾好。
“收好了。”我说,“走啊!”
于是我在她前面蹦蹦跳跳地走出校园。那时从曲塘跑回家要经过万家庄、田家庄、夏家庄、邓家庄、号令庙、马家拐、墩头,最后我与她在曹家庄西边分路,她去曹家庄,我到杭家舍。道路弯弯曲曲,木桥摇摇晃晃。两人总是一前一后,不敢拉开过大的距离,生怕谁走错了路或者掉下河。
从学校出发到万家庄的五里路,走得是轻快的,有时我还轻声地哼着心爱的歌曲。从万家庄到田家庄的五六里路,就渐走渐慢了,书包也渐背渐沉。田家庄南边有个破败的石坊,土路边还残留着几块方方的石头,走到那里,总是禁不住要坐下来歇一会儿。这一坐下便感到两条大腿发酸发疼,但也不敢久坐,因为还有三十里路,于是又起身赶路。从这里往北,河渐渐多了,宽了;桥也渐渐多了,长了;那小木桥,摇摇晃晃的,两个人一起走上去,晃得更厉害了。总是我先走过去,她在河南看住我,然后她再走,我在河北看住她,两个人都走过桥了,再一起赶路。
这时书包越来越重,背带嵌在肩上的肉里,我从左肩换到右肩,从右肩换到左肩,越换越沉,腿子也越来越酸疼。歌曲不唱了,眼睛总是望着前方远处的树木和房屋,心中总是不断地鼓励自己,走快点儿走快点儿,前面就是夏家庄了,小跑了几步,腿子越来越搬不快,只好慢慢挨(挪动),这么挨过了夏家庄,终于把书包放在路边,坐下,蒋静兰也巴不得似的,随即坐下。深秋,昼短夜长,太阳一滚的下子,已经到了西边的中天,小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继续向前挪动。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越挪越慢,终于挪进了邓家庄。那弯弯的土路两旁,散散地住着一些人家,我很想在进庄的那户人家门前,借张凳子坐下来歇歇,要口水喝一下。但前面的路还很长,在这儿不能多歇,不然,天黑之前就不得到家了。心里这么想着,便挪过了这户人家。“加紧走吧,到拐弯的那户人家门前就坐下来歇。”心里又这么想着。挪到那里,心中还是想:“前面的路还长,如果在这里多歇了,天黑之前就不得到家了。”于是鼓一鼓气,又向前挪去。就这样,终于挨过了邓家庄,算算,路程走过了一大半。
邓家庄东边到号令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足有二三里长的土路。放眼望去,灰濛濛的简直接到天边,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呢?我盼望有一位好心的大人,像大姐一年多以前驮我去考初中那样,驮我走过这条路。可是路上只有我和蒋静兰两个人,她早就说脚板疼,现在走得越来越慢了。有时还要我停下几步等她。朝两边望去,远处的麦田里,只有几只寻食的乌鸦,在忽起忽落,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时,书包像有千斤重似的,我把书包挂在胸前,用双手兜一会儿,放下来,再兜一会儿,再放下来。终于到了号令庙。号令庙是个荒凉的地方,有些怕人的传说,我们不敢坐下来休息,咬一咬牙,两人又继续向马家拐挪去。到了马家拐,终于忍不住在路边坐下,看看西天那挂在树梢的一轮红日,不敢久坐,又起身向墩头赶去。就这样,在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我们终于走过墩头,到了通往曹家庄的大路上。这时双腿酸疼得让我想哭,但是,我想到妈妈一定站在门前向这条大路上望,一定为我准备好了热腾腾的晚饭。于是,我鼓一鼓劲,又向前走去,终于到了曹家庄西头,互相约定第二天下午回校会合的地点,并各自向自己的家中挪去。
像这样的艰难跋涉一个月我们至少两次,我以为,这不仅锻炼了我的腿力、体力,更磨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这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将被单、衣服和一些书本打成一个像解放军背的背包,背在背后。当时体重只有49市斤的我,背起这个有十多斤重的大背包,从曲塘一直步行到杭家舍家中。出发时,班主任章季子先生关切地问道:“你背得动吗?”到家时,母亲说:“有本事了,背得动这么个大包袱!”其实,我是咬着牙一步一步挨回来的,因为前面有个美好的所在——家,鼓舞着。
初中毕业后,我和蒋静兰就分手,再没有见过。此后30年,我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像我曾经走过的那乡间小路一样,曲折而漫长,但我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走过来了。
40多年后,我在新华社深圳支社新闻影视中心工作时,一位自称会看手相的文人拉起我的手说:“你食指比中指粗,你这人毅力强。”我是不相信手相之类的东西的,我想:我如果不经历赶路这类事件的艰苦磨炼,我会天生有较强的毅力吗?
陆兆荣,海安人,比我大四五岁,西装头,大眼睛,白衬衫,右足有点跛。学习非常认真,做事非常认真,写的字非常漂亮,他的数理化作业,老师常常拿出来展示,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是数一数二的,他与我无亲无故,但初中三年里他一直帮着我。
我最初跟他打交道是跟他学习四角号码查字法。在王家楼那狭小的天地里,他竟有四角号码字典,我报出一个字,他随即就能说出号码,我很快就能查到,我感到神奇极了,于是他说:“我教你。”不久,我在他的辅导下就学会了,从此,我喜欢上了这位大哥哥。此后,我有不懂的问题都喜欢去问他,他也乐于教我。他教我画水彩画,并给我的英语书上的几好幅插图着了色,他还教我打乒乓球。
我一打乒乓球,便痴迷上了。在王家楼时,有一段时间,一到活动课,就伙同几个人溜到近邻胡集区公所里打乒乓球。由于痴迷,便很有长进,但陆兆荣不知道我进步这么快。一天,我们又在打乒乓球,陆兆荣也去了,他见我帅里帅气、盛气凌人的样子,卑夷地朝我斜了一眼,便走了。那一眼传递的信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过分张扬,好表现自己。这一眼我一直记得,并且也让我有所收敛,但是,我一直没有能够将好表现自己的缺点改正过来。自从跳了级以后,我一直是班上最小的“小不点儿”,当干部一直没有我的份儿,而我成绩还不错,家人、亲友和一些老师一直夸赞我,于是骄傲自满一直与我为伴。人总有表现欲,而骄傲自满的人表现欲就更强烈。于是,上课总是抢着发言,考试总是要交头卷。久而久之,就表现得做事浮躁,口无遮拦,胸无城府,使我这一辈子受害不浅。
初中毕业后,陆兆荣考取了一所较好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徐州一家农场工作,成为技术权威。文化大革命中认为技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他因此被迫害死了。
初中毕业时,他送给我一张二寸的半身照,我一直保存着。西装头,大眼睛,白衬衫。文革快结束时,我才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听到噩耗后,我在他照片后面写了8个字:斯人已去,音容长存。
“我教你。”现在,我写他时耳边又响起他那亲切的声音。
蒋琪和我都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但他个子比我略高一点,走起路来,头昂着,身腰挺直,显出“小大人”的样子,所以在人们的眼中,他显得比我成熟些。我们不仅同班,还长期同一个宿舍,到了上初二之后,每晚睡觉前,宿舍里的那些大同学,总会讲些很“春”的故事,包括蒋琪的两个李堡同乡林杰和缪国琏,但蒋琪不讲。他总是显出很有修养的样子,我跟他同学三年,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
初中毕业后,我们都到南通读高中去了——他在南通中学,我在南通市第一中学——曲塘中学那一届初中毕业生中,只有我们两人在南通读高中,于是星期天,我们常常会会面,谈学习,谈生活,谈过去的同学和老师,“他乡遇故知”,我们的友谊在他乡的土地上日渐加深。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
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先是做党校教师,后来升任为政府官员,官至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
但他没有忘记我,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1977年,我就收到他从哈尔滨市委党校寄来的信,传达了当时还未公开的一些信息给我,鼓励我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我写长信给他叙述我的情况,感谢他的关心。以后我们书信不断。
1989年,我总结自己多年的写作教学经验,写出一本书稿《写作与创造力》,他帮我联系出版社,找编辑。书稿通过后,又带着责任编辑帮我在哈尔滨跑印刷厂,始终没有要我花1分钱使我的这部出版了,并且获得了1300多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我几个月的工资。我要感谢他,他什么也不要,一直使我过意不去。
《写作与创造力》的出版,提高了我的声誉,提升了我的信心,使我此后又出了好几本书,我对他一直怀有感激之情。
前年,他的老父亲去世,我们通了一次电话,友谊虽然还在,但毕竟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我隐隐感到我们中间有一层当今社会带给我们的隔膜。本来,我一直多次邀请他来我家作客,好好叙叙旧,但现在也不敢蓦然开口了。
我常常想,如上帝让我高中毕业后也上到大学,今天我又会是怎样的呢?在高中里,我的成绩也不错啊!那年,全国的高中毕业生是不够大学招生的啊!
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