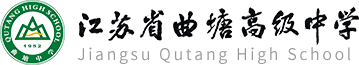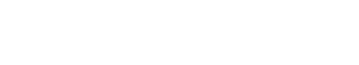betway必威登录
教育论文
戏中戏:论《十二楼》独特的“设局”技巧
戏中戏:论《十二楼》独特的“设局”技巧
摘 要
《十二楼》是清初杰出的小说家、戏曲家李渔的代表作,作为一名技巧型作家,李渔在《十二楼》中全面而自觉地使用了“设局”技巧。原因主要在于“设局”可以满足作者“求新求奇”的创作需要。“设局”技巧的具体应用对小说中人物塑造、文本叙述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此外,从“设局”技巧的使用还可窥见作者的智慧哲学和自娱娱人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十二楼,设局,技巧
引言
《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觉世名言十二楼》,是清初著名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拟话本小说集,全书计十二卷,每卷演一个故事,每篇故事中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与情节的展开多与那座楼阁有关,合起来称十二楼。这一十二则小说单个看具有个性美,合起来又自成体系,具有整体美,足见作者的独具匠心。
李渔小说数量不多,且多为短制,但却奠定了其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李渔对小说文体的独创性,除了具有一种创新求变的理念,在创作技巧上他也不断创新。相对此前创作的小说集《无声戏》而言,《十二楼》在创作技法上显得更为自由和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设局”技巧在文中的大量使用。
“设局”即“设置圈套”,在《十二楼》中“楼”是为情节而设置的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局”则是小说人物生活活动的过程,楼中有局,如此时空交错,为读者演绎了一场场绚丽多姿、光怪陆离的人间悲喜剧。
一
在《十二楼》中,李渔大量而频繁地运用“设局”技巧,屡试不爽,显得全面而自觉。究其原因,主要是求“新”求“奇”的创作需要。
李渔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关目新奇,追求尖新奇巧的艺术效果。清人刘廷玑称赞其小说“造意创词,皆极尖新”,近人
“渔自解觅梨枣以来,廖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时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1]
他曾言:“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因而对创作小说是严肃并且有主张的。其中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无声戏”,即认为小说是无声的戏剧,可见他是用戏曲理论来指导小说创作,因而他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在清初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取得较高的成就。
在李渔看来,求“新”即是求“奇”,而所谓的“奇”主要指故事情节方面,
“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2]
小说既为“无声戏”,那么当然也要讲究“新奇”的效果了,就本质而言,就是要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而讲究“奇”、“戏剧化”的特点,其实并不仅是戏剧创作的专利,李渔小说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此前话本小说的影响。说话伎艺存在于市井的勾栏瓦肆之中,具有较强的娱乐目的和商业性质,是一门“听觉的艺术”。话本作为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倘若没有动人复杂的情节和强烈的戏剧性,将无法吸引听众和读者的注意,因而极为讲究“戏中戏”、“奇中奇”。如此看来,小说与戏剧同样求“奇”,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李渔是深谙这一点的。
但与传统的话本小说不同的是,李渔在创作时,逐渐舍弃了“宿命、灵怪、因果报应”等主题和题材。而是推崇从“常中出奇”,重在突出“人世之奇”。他以为,
“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即所谓:“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情理之中,奇莫奇于此矣”。[3]
这一点在《十二楼》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小说既要“出奇出新”,又不谈神鬼报应,李渔创作的途径之一就是求诸新的创作技巧。一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李渔是一名技巧型的作家。如李时人谈到 “李渔是个偏重技巧型的戏曲家,而他又将这一点带入了他的小说创作”。[4]
“设局”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是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用“设局”表现“人情物理”,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李渔“常中出奇”取材的观点。另外,“设局”常令人捉摸不透,其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也易收到令人惊奇的效果。对生活细节敏锐的洞察力和感悟能力使得李渔对“设局”技巧情有独钟。其实这一技巧李渔在《无声戏》中已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在《人宿妓穷鬼嫖冤》里就描写了一位富于正义感的下级军官司设局帮助一机位痴情的理发师从负心的妓女那里索回被骗钱财的故事。又如《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从故事的命名可知其中采用了“设局”的技巧。到《十二楼》中则几乎篇篇都在运用这一技巧了。
另外,清初话本小说已摆脱了口头文字的样式,进入了文人化和书面化的阶段,成为了真正的案头之作。其实在产生了“三言”这样一部对宋元旧篇进行编创、整理的集成之作以后,拟话本创作就逐步进入了文人独立创作的阶段。像“二拍”、《西湖二集》等拟话本所依傍的原始材料已不如冯梦龙时那么丰富完整。凌濛初就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只好“取古今来杂碎事”“演而畅之”。其中“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5]到李渔时,可供借鉴的材料已是非常琐碎了。《十二楼》中的事故大都“记当时见闻,或是凭空结撰,或者是自寓”。 “设局”这一技巧有助于李渔的艺术虚构和创作需要,它就犹如一根锋利的针,可将众多零碎的材料有序地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设局”技巧又可将作者的想法、经历做一些适当地加工自然而然地融于小说之中,从而使作者能够借小说这只“酒杯”,来浇心中之块垒。
二
与传统技巧如“悬念”、“突转”、“巧合”等相比,“设局”技巧显得颇为独特,它不但塑造了一系列聪慧的人物形象,而且对整个小说文本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十二楼》中,李渔竭力塑造了一类“奇人”—“设局者”,他们中间有高高在上的县官,有路见不平的侠客,也有大户人家的婢女,甚至还有到处行骗的拐子。这些人不论身份的高低贵贱,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聪慧,作为“局”的策划者的执行者,他们大多心思慎密、工于心计,富于心术,往往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达到目的或解决问题,是平民中的“英雄”。并且他们有主见,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如《合影楼》中的路公,书中称“他的心体,绝无一毫沾滞……合着古语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间’。”《鹤归楼》中的段玉初“自幼聪明,曾噪神童之誉……总是他性体安恬,事事存了惜福之心,刻刻怀了凶终之虑,所以得一日过一日,再不希冀将来。”李渔着力刻画了这些“设局者”,突出其“聪慧”,并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另外,“设局者”往往采取温和的手段,使被骗者心甘情愿地走入“局”中,而不是通过抢劫、胁近等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曲折委婉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李渔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温柔敦厚的思想。
话本小说大多采用一种全知全觉的叙事模式,书中的叙述人大都借用一个全知全能说书人的口吻,他对故事中的人物,发生的事件无所不知,充当了一个无所不知“上帝”的角色。《十二楼》对这种叙事模式有所突破,它部分地采用了限制性的叙事模式。这与作者在小说中使用“设局”技巧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以《闻过楼》为例,故事中顾呆叟的身上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奇事,莫名被点重差,又无端被强盗抢劫,最后竟然又被诬通匪窝赃而遭拘捕,祸事一桩接着一桩,且越来越严重。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叙述者与读者一无所知,只是跟随着顾呆叟走。叙述者只能看到人物的外貌言行以及所处的生活环境,但并不知道人物的动机、目的、情感以及思维。书中人物也局限在自己的视野范围,而读者只能去猜测、联想,到故事的最后一刻才知道真相。由于“设局”即是在设置一个圈套,作者在讲述过程中,不宜面面俱到,倘若将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可能就会失去令人新奇的效果。采取限制性的叙事模式可以牢牢抓住读者的心理,引导读者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也一步步地走入了“局”中,又一步步走出“局”来。
此外,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以情节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话本小说大都为“情节小说”,从“设局”到“解局”之间有一个过程,其中又可穿插人物的介绍,故事背景等,这与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往往会暗合,或成为情节的某一部分,换言之,“设局”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对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加强了小说的戏剧化效果。
三
“设局”技巧的大量使用使作品新奇有趣,情节跌宕多姿,扑朔迷离,的确为小说创作增色不少,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一)人物形象塑造受到了影响,显得不够丰满
由于人物根据故事中的“局”而设置,因而在小说中始终处理相对次要的地位,又因为作者过于注重人物在故事中设这样那样的局,而相对忽视了对人物其他方面的刻画,使得人物形象塑造相对薄弱,所以故事中的人物大都是“扁平人物”,其性格往往成了故事的附庸。
对于故事中那些聪慧的“设局者”,李渔着重突出了他们“智慧”的一面,却无意中损害了其道德,显得有些弄巧成拙,如《拂云楼》着力刻画一艳婢能红,极写其聪明才智。能红设策为心上人裴七郎出谋划策,将韦姓一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显得能红太巧太能,而韦姓太愚太庸。更有甚者,后竟令裴七郎假做恶梦设局欺骗小姐换得自己一席之地,私心滔滔,聪明有余,可爱不足,与西厢记中红娘何异于天上地下?实难博得读者的喜爱,又如《夏宜楼》中瞿佶用“千里镜”窥人闺室,心术已是不正,又想方设法欺骗小姐,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夺锦楼》的袁秀才虽是才气纵横,但他替人代考,公然舞弊,可见其人品,作者原意是显其谦让,反而弄巧成拙。《三与楼》中虞素臣好友用计使楼归原主,本出于一片好心,但埋金栽赃把唐家弄得家破人亡,未免有些过分。而《奉先楼》中的舒秀才为了存孤而不顾妻子的死活,已透露出他极度冷酷自私的一面。“设局人”大多心计太重,城府太深,又过于玩弄小聪明,反倒少了些淳厚纯真,往往得不到读者的同情和认可,也难以撼动读者的内心世界。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特别是“局中人”,他们没有主见,堕入“局”中而不自知,被人任意摆布,形如行尸走肉,往往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因而人物形象苍白无力,不够鲜明,作者没有对他们作细致深入地刻画,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二)为技巧而技巧,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郭英德认为:“求新求奇的审美趣味,固然使李渔的小说在题材选择上戛戛独造,但却同时也使他过于迷恋新奇的故事,津津乐道于人物的外在行为,沾沾自喜于表面的道德阐释,而未能深入剖析人物行为的内在动因,披示人物行为的内心矛盾。因求‘奇’而欠‘深’。甚而导致失‘真’。”[6]其实李渔对人物的内心以及行为动因是有所揭示的,甚至是反复权衡,认真考虑过的,像《奉先楼》中舒秀才妻面临守节与存孤的痛苦抉择,李渔在写作之前必然会有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舒氏最终的做法其实也是李渔对社会冷静洞察的结果。
但只顾一味地使用“设局”技巧,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的效果,而不顾读者的内心感受和接受心理,必然会导致作品艺术价值的下降。如《归正楼》中作者似乎夸耀、羡慕的语气写出了一个骗子各种高超的骗术。的确是起到了奇的效果,但作者也失去了自己的立场,陶醉于各种骗术之中,显得善恶不分了。“设局”的人为因素太强,《十二楼》的“奇”从某种程序上是一种“造奇”,是雕琢而非天工,因而总让人觉得技巧性太强,不免有纤巧之弊。无怪沈
(三)设局技巧的过多运用,削弱了话本小说劝惩的效果
“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7]话本小说从产生之日就有着劝惩的功能,李渔沿袭了“三言二拍”的体例,《十二楼》命名为《觉世名言》就是因袭了冯梦龙的“三言”。他自称为“觉世稗官”,对小说劝惩的功能也并不讳言。在〈闲情偶寄〉凡例中李渔明确将“规正风俗”和“警惕人心”作为写作宗旨,另外他在《香草亭传奇序》中还提出文章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这些明显可以看出他的道德劝惩意图。但由于“设局”技巧的频繁使用,使得其小说的劝惩效果大大减弱。正如郑振铎所言,“在《闲情偶寄》里,笠翁有许多对于剧曲的意见,颇可注意,他颇以阐忠说孝为传奇的目的,但同时,他自己的笔端却也不太清白,正像他的‘十二楼’一样”。[8]倘若真把《十二楼》当劝惩小说看,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十二楼》故事人物的命运大多似乎都由“局”而定,万事也变得简单起来,只要设一个局就可以解决,“设局”将一切都简单化了。另外,设局固然是智慧的体现,但总归是“骗人”,计谋如果没有正义的引导,就会堕落为害人的手段。倘若故事中的人物心存邪念,那结果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四
从李渔对“设局”技巧的迷恋和喜爱,可以看出李渔的智慧哲学和他自娱娱人的创作心态。
“设局”作为一种计谋被李渔不厌其烦地详加演示,由此可见他所欣赏和崇拜的是一种有智慧的人。《十二楼》中人物没有凭借权势等外力来解决困难,而是依靠自身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才智,且不分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如《拂云楼》中的婢女,《归正楼》中的拐子都是其赞赏的对象。在小说中人物虽是为“局”而设的木偶,但他们的命运却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当小说中人物面对困难,遇到阻力时,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积极地寻求解决的方法,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如《夏宜楼》中的瞿佶人,《拂云楼》中的裴七郎都是如此。的确,在明清之际,受到李贽、王阳明等人的影响,形成了一股反理学的进步思潮。固有的封建道德已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们开始追求名利来满足世俗的欲望。那种治国安邦的宏大抱负已被追求世俗的利益所取代。人们更多欣赏的是那种能解决问题的凡人而非圣人。另外,李渔一生托钵,经常出入缙绅贵族之家,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与人打交道,要博得别人的喜爱和赏识甚至有时不得不维持自己仅有的尊严,他所依赖的只能是他的聪明才智,这一点深刻地反映在他小说中,并成为他小说永恒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楼》中,人物“设局”的动机和目的大多为善意的,故事的发展大多也随着设局而展开,几乎也没有阻碍,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设局”的结果也往往是皆大欢喜。这与李渔的小说娱乐观有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李渔‘无声戏’小说观艺术层面背后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文化内涵,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类的悲欢离合,乃至小说本身也不过是一场戏而已。”[9]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观念使得李渔在创作中更注意小说的娱乐性,正所谓“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
在《风筝误》传奇的结尾李渔写到,“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曲;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他又曾坦言在创作时“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 [10],现实中的李渔是不得意甚至是落魄的,也许他只能在小说戏曲中找到乐趣和慰藉,他内心极不情愿将这心中最后一块净土变为苦难之地。“设局”技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自娱娱人的工具。
参考文献
[1]、[10][清]李渔《李渔全集卷1:一家言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47页
[2]、[3][清]李渔《李渔全集卷3: 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
[4]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 《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5]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8页。
[6]郭英德《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 《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1页。
[9]徐凯《惩劝与娱乐─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发表《特色教育探索》2012.7